提起1977年的那场高考,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略显平静,“大约恢复高考前一年,高中时的一位语文老师对我说,你们这一代人当中,一定会有人凭高考上大学。从那时候起,我就开始了高考准备。”所以,知道可以高考的消息后,她说,自己并没有太大的意外。
1976年,持续十年的“文革”结束。在接下来的1977年,进行的则是一场攸关国运的改革——恢复高考。影片《高考1977》讲的就是那个年代的故事。
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,但对于积蓄了十几届的570万名初、高中毕业生来说,那个冬天阳光灿烂。“考生中,许多人早已青春不再,但在考场上,很多人热血沸腾,激情满怀。”30多年后,王旭烽依然觉得,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……
●亲历者说

杭州市应考高等学校的考生满怀信心进入考场。
没有高考,她也许还在绕线圈
1977年,已高中毕业的王旭烽,进杭州长征无线电元件厂当女工,干的是绕线圈的活。如果没有恢复高考,王旭烽的人生轨迹,也许就这样一直平淡下去。
同年10月,拱墅区组织了一批优秀青年到党校培训学习,文字功底不错的王旭烽幸运地成了其中一员。在会上,老师告诉大家,高考制度恢复了。“好消息宣布的一刹那,许多人都惊喜万分,恍然若梦。” 王旭烽说。
在彼此反复确认消息的可靠性之后,潜藏在王旭烽内心深处的希望之火被点燃了。
“仿佛一夜之间,蒙尘多年的中学课本,变戏法似地从大家的床底下、墙旮旯、废纸箱里冒了出来,到处传阅。”王旭烽记得,从消息公布到参加高考,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。
“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学习。白天上班时,厂里领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让我们偷偷摸摸地看书。午间休息时,一帮准备高考的人聚拢来,一起查漏补缺。”王旭烽说,他们很注意劳逸结合,午饭后会先玩一会扑克,谁输了谁就去洗碗,其他人就开始复习功课。
王旭烽当时留了一条齐腰的长辫子,因为学习时间紧迫,根本没时间洗这么长的辫子。于是,她买了一条土黄色的围巾,把自己的长发包起来,一个多月没洗,“我告诉自己,如果考上大学,就把辫子剪掉。”大有破釜沉舟的勇气。
“当时最欢欣的,还是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们,他们纷纷奔走相告,也预感到命运即将改变。”王旭烽说,“所有的有志青年,都有拨云见日般的清朗感觉。”
拼命读书,想补回失去的时间
1977年的高考,各省分别进行,没有全国统考。浙江省分初试和复试。
1977年12月25日,是复试的日子。王旭烽记得非常清楚,那是个晴朗的冬日。王旭烽还对几个考题记忆深刻:“考了‘三民主义’等几个名词解释。由于荒废了10年,很多考生的文化底子并不好,甚至有人把‘三民主义’和‘三光政策’给混淆了”。
一个多月后,高考放榜,王旭烽被杭州大学历史系录取。从进入大学的那一刻起,那代人就成了追赶时间的一群。
“我们拼命读书,想补回失去的时间。”那种急切与渴求知识的心情,可能是现在很多学生无法理解的。“学校里的书店一旦有新书上柜,店门口准能出现百米长队,甚至还有通宵排队的。”因为买不到电影文学剧本《莫斯科不相信眼泪》,王旭烽从图书馆里借来,完完整整地抄了一遍。现在她也会时常回想起墙报栏前,抬头踮脚,借着手电光仔细阅读的身影。
“那时候,大家拼命看书、辩论、思考。”1978年底,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立刻成了大学生们讨论的热点,“吃饭、卧谈会,全是这个话题。”王旭烽清楚地记得,一位同学把她约在篮球架下,讨论了3个钟头的五四运动;另一位则约她到西湖边,大谈了一个夜晚的“历史进程的动力”。 如今,他们两位,一位是大企业家,一位是资深教育工作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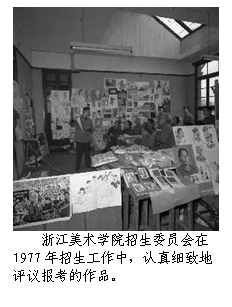 不论长幼,皆“以天下为己任”
不论长幼,皆“以天下为己任”
“我给他们讲人类的起源、古埃及神庙、原始文字……”后来担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省文物局局长的毛昭晰先生,是当年杭州大学历史系的老师。“我看到他们脸上那种欣喜,眼神里满溢着对知识的新鲜与渴求。”
毛昭晰还记得,那一届杭州大学历史系分两个班,有70多个学生,年龄参差不齐,最大与最小的相差14岁。“年纪最大的金儒宗30多岁,身为农民的他,已有3个孩子,上大学前,几乎天天都在农田里忙活;而当时班里年纪最小的龚国庆,才不过十几岁。”毛昭晰回忆,当年的高中应届生仅占百分之十。
因为是“文革”十年后首次招考,且招生的年龄放宽,大量“文革”时的中学生,报名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。“这批考生虽然年龄偏大,但生活阅历丰富,学习极其刻苦,”毛昭晰说,他在长达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,唯一给的一个满分,就是给了一位从“知青”报考上来的学生。“他的每一题均是一篇短小精美的文章,内容正确、文字流畅,几乎挑不出任何错误。”
77级把“文革”十年中被耽误的人才汇集到了一起,而不同的年龄阶段,有着不同的社会阅历、人生感悟和知识背景,在四年的相处中,大家不断进行思想交流和碰撞,每个人都受益匪浅。
“那时学生们的课余活动也很丰富,话剧、体操、排球、文学社等社团,都在校园里开展得红红火火。”毛昭晰强烈地感受到,这一批学生忧国忧民,身上有着很明显的“以天下为己任、创造历史”的激情与情怀。“这在他们日后的事业发展中,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至今,杭大历史系77级的学生里,集中出现了10多位知名地产商、两名福布斯富豪、一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。”
多年之后,当同学们再次聚首时,他们端端正正地坐好,邀请毛老师再给他们上一课,因为,为他们讲大学第一堂课的老师,正是毛昭晰。
“1977的高考远远超出了考试的意义,它对整个社会有拨乱反正的作用,是一种价值的重建。”作为一名老历史学家,毛昭晰如此感叹道,“犁者,耕耘之器。高考犁铧过处,结土松动,金玉良才毕现,荒原气象一新。”
摘自《今日早报》
记者 王湛
实习生 陈譞懿
2009年9月20日